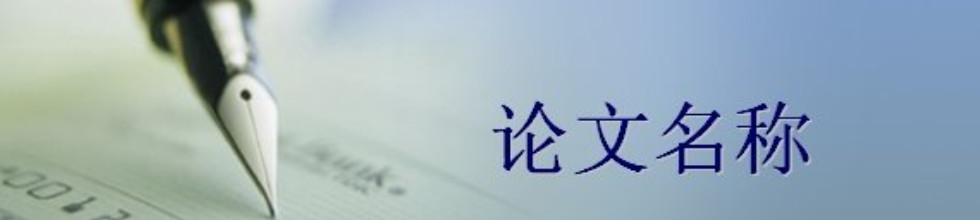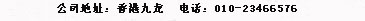陈龙海一片雪日本传统审美文化的多棱
陈龙海,男,年5月生,美学博士,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日本“情爱大师”渡边淳一的小说《一片雪》是日本文学传统沃土上绽放的现代之花,其中折射出日本传统审美文化的多维镜像。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发:其一,作者张罗的一场场爱欲筵宴,表达了日本人对自然人性的绝对尊崇和典型的日式情爱观;其二,以一年为叙事时间和季语为回目名,反映了日本人对岁时季节的敏感和由此引发的人生感怀;其三,以花喻人、以花言情,体现出东方审美同情观;其四,以“一片雪”作为小说名,“雪”则是美与“物哀”的双重隐喻。
关键词:渡边淳一;《一片雪》;传统;日本审美文化;隐喻
在日本当代作家群中,渡边淳一是一个值得研究作家。究其原因,就在于,作为日本现代情爱大师,他所有的写作,都试图坚守纯粹的日本范式,他将《源氏物语》以来的日本文脉延续至今,表现了典型的日本美;他的创作场域始终没有离开日本文学的传统空间,是日本传统审美文化沃土中绽放的现代之花。众所周知,日本作为一个传统的现代国家,可以说是裹挟着传统走进现代的,无论是“明治维新”,还是“脱亚入欧”,在其近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其传统的血脉一直延续不断。本文试以渡边淳一的《一片雪》为解析文本,从日本传统美的位置出发,在无声飘落而又悄悄融化的那一片雪色中,经由对男女主人公短暂而销魂爱欲的凝神静观,从一个看似简单的情爱故事中,寻绎出隐喻其中的日本传统审美文化的多棱镜像。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推进,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文明互鉴,也会不断升级和提速。对于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言,坚守本民族文化立场,深刻领悟“越民族,越世界”的文化真谛自然显得比任何一个人类发展时段都重要。关于这点,渡边淳一的写作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爱欲的筵宴:日本情欲美的张扬
在渡边淳一的长篇小说中,《一片雪》远不如其成名作《失乐园》那样引起过轰动效应,也不如《无影灯》《光与影》《钝感力》《遥远的落日》等那样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这是一部情节简单、涉及人物较少、时间跨度较短、叙事手法也不复杂的小说。小说的男主人公伊织是一个“年过四十有半”的建筑设计师,在东京开设了自己的建筑设计所,当事业有成之际却遭遇婚变。于是,他从家里搬了出来,寻求婚姻外的性爱。当此之时,伊织与28岁的相泽笙子已有四年的恋情。后来,伊织邂逅了比相泽笙子大七岁的高村霞——一个有妇之夫(她的丈夫是个画商,在银座和镰仓都开着店),在他们的第三次见面后,便有了肌肤之亲。从此,伊织便开始了与三个女人的情感纠结,三条线索,偶有交集,平行推进,像一把琴,鸣奏着不同的音符,却奇异地组合成情爱和声。为叙述方便,分别来说:
一、伊织与妻子处于分居的状态,在整部小说所展示的时空范围内,她一直隐身其后,小说基本上没有提供关于她的信息,比如她的家世背景、受教育情况、兴趣爱好,等等,我们一概不知。至于她与伊织的情感矛盾,小说始终不著一字。除了与伊织有过一次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电话,她就一直“缺席”着。她与伊织是通过朋友介绍相识并结婚的,对伊织看来说,“他并非特别喜欢她,但也说不上她有什么不好。虽然相貌没有惊人之处,但娶作妻子,倒也放心”[1];“已经不再有爱情,即使留个形式当夫妻,也毫无意义”[2]。而他的妻子,开始是不同意离婚的,后来由她的弟弟村井康告知伊织她同意了,一段与爱情关涉不大、波澜不惊的婚姻就此画上了句号。
二、伊织与妻子分居一年多,但他与女秘书笙子已有四年恋情。虽然这种情人关系还在继续,仍有约会和做爱,但因高村霞的介入,她已明显退居次要位置。不可否认,他们深爱过,但对于伊织来说,与高村霞相比,他对笙子的迷恋似乎更多在于她的肉体。当他们最后一次做爱后,笙子哭着告诉伊织,她与建筑设计所职员宫津等去山阴旅行时被迫与宫津发生了性关系。伊织不能原谅笙子,导致了笙子的辞职,并最终嫁给了宫津,这段恋情也就随之结束。
三、伊织与高村霞的爱欲沉湎是小说的主线和主要情节。高村霞是画商的妻子,富有教养,优雅妩媚,温柔多情。老夫少妻的婚姻模式,商人重利轻别离的生存状态,使高村霞这个闺中少妇识尽了“闲愁”滋味,情感和性欲的双重压抑与缺失,必定需要舒张与释放。她与伊织本来像行走在平行而绝无交叉的人生轨道上,因为伊织热衷美术,还为报刊写作一些美术随笔、评论之类的文章,并每周到大学讲一次课的缘故,促成了这两个陌路人的邂逅,而此时的伊织正处于分居的节点上,这对男女似乎注定要上演一场风花雪月的活剧。渡边这位情爱写作大师,在小说的每一个章节都为伊织和高村霞张罗了肌肤之亲与鱼水之欢,从东京伊织的公寓和酒店、京都和奈良的旅途,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奥地利维也纳的欧洲之行,中心“事件”始终是做爱。无论是伊织的建筑设计,还是关于美术的话题等等,似乎都是为他们做爱所作的铺垫;无论是东京的街色,还是京都、奈良的景致,以及阿姆斯特丹、维也纳、斯拉方教堂的文化等,都是为他们做爱所营造的氛围,为这出情爱剧点染的各式色彩。高村霞由最初的矜持、沉稳、害羞到逐渐在“羞耻与淫荡”之间把握微妙的平衡,直至到欧洲旅游时与伊织同浴,并“达到极致”。三条线索,实则是伊织与高村霞和笙子两个女人之间的情欲纠葛。作为男人的伊织,他认为,“虽说已是中年,但男人萌生出作为雄性的欲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作为雄性,产生那样的欲望,也许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了。从某种层面上讲,至少这样的男人比那些对异性毫无兴趣、却为同性相吸的娘娘腔男人更好些”。[3]既然“合情合理”,那似乎就无可厚非。而作为有家室、有事业的男人,作者以细腻深婉的笔触,深入到伊织内心:
莫非工作热情和迷恋女人的激情同出一辙……
如果没有足够的热情,就不可能迷恋并且征服女人。特别是已有家室的人,更需要特殊的耐力。不管比喻是否恰当,伊织对女人确实有一种类似完成项目时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持久力。……如果只龟缩在常识和伦理的范畴里,那么无论做任何事情,他都会易于处世,并且容易被社会接纳。他本人感到轻松,而且也不必花费精力。但是,结果只能是一生平庸,随波逐流。
伊织却不想平平庸庸地过一辈子。他虽然并不希望平地起风波,但他始终认为挑战意识是一种动力,能够推动他的工作和爱情生活。[4]
这就是伊织的告白:他不想过平庸的人生,就不可能“龟缩在常识和伦理的范畴里”,而且他的所作所为正是挑战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他将热情同时付诸于工作和迷恋女人,而征服女人,需要特殊的耐力和“持久力”,如同对待工作,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虽然伊织也时时感到内疚,内疚于对待家庭,尤其是他的两个女儿,内疚于高村霞的丈夫,但在他貌似“有理”的人生哲学的观照下,内疚感随之烟消云散,他依旧有“持久力”地迷恋别的女人,腾挪辗转于她们之间,在肉欲纵横中乐此不疲,欲罢不能。渡边就这样为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张罗了一场接一场的爱欲筵宴,任凭自然人性的欲望横流。
将渡边淳一称作“情爱大师”,自然不无道理。但在日本这样的国度,古今写作者,几乎都是可以获此“殊荣”的,如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和《伊势物语》中露骨的色情铺张随处可见。到了江户时代,著名作家井原西鹤因长期流连于风月场中而被冠以“好色作家”的“雅号”,其“好色系列”小说《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代女》等更是在市井中广为传播,祝大鸣说:“这些作品都以江户时代町人阶层的婚恋和家庭生活为主要题材,以生动鲜活的性描写为特色,涉及情欲、肉欲、妓女、同性恋,赤裸裸的色情描写是必不可少的‘段子’。在井原西鹤的小说主人公看来,性,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是人性的组成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自然的,谈不上罪恶感和羞耻意识。”[5]现代日本著名作家中,不少都是色情写作的高手,如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作品中大量的婚外恋、不伦之恋、畸恋、同性恋、变态恋、人鬼恋等,几乎无所不用其极,而其中细致的色情描写也比比皆是。相对来说,渡边淳一《一片雪》的写作还是相对节制的,对性事的描写还保留着适度的含蓄,极少有细节的描摹,甚至遣词造句都力图“文雅”,点到即止,远不如他自己的作品如《爱的流放》《失乐园》中那些色欲描写的淋漓尽致。于是,肆意的铺张与含蓄的笔致就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在此张力场中,无论是高村霞的肉体美,还是伊织与高村霞的灵肉之欢,都达到了一种“雅”的境界,作者所极力张扬的正是这种典型的日式情欲美。
要准确解读《一片雪》中的爱欲主题,就必须深入到日本性爱主义文学传统中,而这种文学传统(思潮)的形成自有其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对此,叶渭渠做了精辟的分析,一方面,“神婚”是日本爱欲性文学素材的起源,“日本神道对爱与性的这种宽容态度,不仅影响日本人对爱与性的伦理观,而且影响着日本文学的审美情趣”[6];另一方面,“日本古代文学的好色表现,是在一夫多妻制下的一种恋爱情趣,一种抽象的美理念”。[7]在平安、江户、镰仓时代,好色理念是被社会广为接纳的,“好色是美的恋爱情趣,健康的道德情感,多角的男女关系,这是一种风流的游戏”,甚至“是日本贵族社会的一种文明的理想”。[8]基于此,亦如叶渭渠言:“如果用现在一夫一妻制的习俗来审视,是很难理解古代日本文学这种深沉而悲哀的恋爱诸相中所展示的美;如果用儒家的道学观念来评判,就更难理解日本古代文学的好色思想所包含的丰富多彩而深刻的文化内涵。”[9]日本人在接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既排斥了佛教的禁欲主义,也罔顾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道德伦理规范,而表现出对人类的天性的绝对尊崇,这种思维特征表现在审美思维中,就是对人类自然情感尊崇和对两性肉体快乐的倾慕渴求和赞美。著名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作过长期考察,在她的著作《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中认为,作为佛教大国的日本,应该遵循古典佛教的信条,并形成相应的伦理道德戒律,“似乎理所当然地会把个人的欲望看成一种邪恶,应该从人们心中除掉。……令人奇怪的是日本的道德戒律对官能的享受竟如此宽容。……日本人并不认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是罪恶,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享受是正当的,而且值得提倡。人们追求并重视肉体享受。”[10]可以说,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追求并重视肉体享受”,不以为“耻”,反以为“美”的,恐无出日本人之右者。
渡边淳一的《一片雪》只是日本性爱主义文学传统历史延长线上的一个小点,也是日本审美思维的感性显现。小说中多角的男女关系及其重复变奏的情欲描写是极其自然的,不仅与“罪恶感”和“羞耻意识”无关,不能用世俗的伦理观来评判,而且是一种美的情趣,作者是以一种赞赏的态度来加以表现的。虽然小说的主线是做爱,但其蕴含的文化艺术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如日本的建筑文化,日本的舞蹈,马蒂斯的绘画,东京、奈良、京都等地的风景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奥地利的维也纳等地的文化特征,还有形形色色的插花艺术等等。对高村霞的描写:富有教养,妩媚温柔;与伊织约会及旅游时,大多身着日本古典美标识的和服;做爱时总是要求垂下窗帘,这不仅是她的矜持和含蓄,而与日本人崇尚的“阴翳之美”有关;她还深谙插花艺术,将每一次约会和做爱渲染得浪漫和唯美。总之,伊织与两个女人之间的爱欲缠绵,是一种美,一种典型的带有日本民族特征的审美理想的美。
二、岁时季节:由敏感心灵生发的人生伤感
《一片雪》的叙事时间跨度为一年——始于春天,终于春天。小说的回目,既不是数字顺序编码,也不同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形式,而采用了带有日式情味的“季语”,依次为:“山茶”“长昼”“双夜”“春愁”“余花”“嫩竹”“青芒”“秋思”“花圃”“秋风”“良宵”“寒露”“冬野”“薄冰”“花冷”,计15部分。
日本的“季语”最早的来源应该是中国。作为一个小农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国度,季节时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从《说文解字》中对“年”的解释“熟谷也”即可知。中国人历法,其内容十分丰富,凡日月年岁、四时、分至、阴阳合历、纪年法、节气、月建、纪日法、纪时法等皆囊括其中。此外,中国人还发明二十四节气,农业的播种与收获等一年的完整周期无不与此密切关联。农耕在日本的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接纳中国文化的过程中,经过筛选,中国的历法、节气等都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资源,并由农业生产进而影响到日本的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在日本的《万叶集》中,始有春夏秋冬四时的详尽记载,《源氏物语》中就有“帚木”“松风”“槿姬”“蝴蝶”“新菜”“柏木”等回目名。在最能体现日本文学特色的俳句中,季语更是大放异彩。可以说,日本文学中的季语是中国历法、节气等的简化和发展。一般来说,日本的季语与四时的天文、地理、时令、动物、植物、以及应时行事有关,由此也反映出日本人在吸纳外来文化时的自主创造。
季语之于俳句,不仅是其重要内容和结构要素,而且可以说是俳句的灵魂,并成为其审美传统习惯。林林认为:“季语,广义地说也是景语(这个词儿《文镜秘府论》用过),景语与情语不免发生接触,即从自然界及社会上的客观景物和作者主观感情的交融,从各种观感通到心灵,触景生情;或是移情入景,即作者选择适合抒情的景物,以至化无情的景物为有情,使客观的景物,变为主观思想感情加工了的景物。”[11]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比比皆是。然稍有不同,中国的文人似乎对春、秋的感触要多一些,或伤春、惜春、悼春,或悲秋等等。虽然也有对夏、冬景物的描写,但其中所注入的情感似乎不如春、秋之浓烈、深沉和隽永。而日本人则是对四季都同样的敏感,同样能牵动其神经,撩拨其情感,并在文学,尤其是俳句中予以细腻、深婉的表现。正如邱紫华所言:“日本的气候四季分明,季节变化带来的事物形态的不同色彩的变化非常明显,例如大海的各种形态、树木的各种色彩、风的大小及风向的变化、农作物的生死荣枯等。这种变动不居的自然形态,促成日本民族对对大自然‘变化’的高度敏感。儒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和佛教的无常观念传入日本后,更增强了日本民族对人生世事变化无常的感受和反思,从而确立了诸行无常的人生观和变动不居的自然观,并引申出对瞬间状态的深深留恋和对生活中许多不期而遇的事物、机遇不禁感慨万千的民族情愫。”[12]另外,日本列岛所处的地理位置,像孤悬在太平洋上的一叶扁舟,地震、台风、海啸如同家常便饭,大量的活火山的存在,不知何时就会爆发,频发的自然灾害使日本人从来就缺少安全感,人类生命在大自然的淫威面前显得无限渺小和脆弱,无数生命的瞬间消失和伤残的事实,使得日本人对生命无常有了刻骨铭心的惴惴不安,留恋生命而不可得的人生常态;日本人的心灵格外细腻,对四季更迭格外敏感,于是,催生了一个多愁善感的悲情、忧郁的民族。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一片雪》只是“季语”文化和俳句文学传统的诗意空间中展开的情爱叙说。首先,一年的光景,四时的变化与情感发展相应和。川西政明在《一片雪》的附录《解说——稳固的形式美》一文中指出:“在渡边文学中,随着自然的变化,人物的心理也发生着变化。这是很显著的特征。”[13]《一片雪》也正好显示了这一特征。伊织与高村霞是在冬天相识并有了肌肤之亲的,随着春天的到来,高村霞曾经蛰伏的情欲也渐渐苏醒,但这一期间,亦止于东京来去匆匆的约会与做爱,她与伊织不过如“露水夫妻”,因而,她终究收敛着,矜持着;在夏天的京都、奈良的旅行中,高村霞的情欲得到了初步的释放,也似坦然地接纳和与伊织的灵肉之欢,但还是心存芥蒂,以至于趁伊织熟睡时搬到了另一房间;秋天的欧洲旅行,是高村霞情欲的彻底解放,他们尽情地宣泄着人类原始的自然情欲,充分地享受着男欢女爱的灵肉愉悦,像一首重复变奏的乐曲,终于迎来了它的高潮。此刻,高村霞,“一个沉稳的女人,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个十分放荡的女人”。[14]这一回目名为“良宵”的确也恰如其分。到“寒露”时,正当伊织与高村霞沉浸在爱欲的欢愉中时,笙子不约而至,“撞车”不可避免,伊织“都不想失去”已无可能;在“冬野”里,伊织离婚,笙子离去;“薄冰”已经预示着伊织与高村霞的情缘已如履薄冰;当又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高村霞的婚外恋情终于被她的丈夫知晓,在樱花开放,春雪飘舞的时节,伊织与高村霞的情缘走到了尽头,小说也以“花冷”而画上一个苍凉的句号。对于伊织来说,“这一年确实是动荡不安的一年”,“惊心动魄的一年”,“不可思议的一年”。[15]其次,随着四季的变换和时间的推移,伊织丰富复杂的内心感受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一开始,他是纠结、困惑和矛盾着的。作为有妇之夫,作为父亲,他觉得与高村霞这个有夫之妇的情欲缠绵有一种内疚感,甚至觉得“罪孽深重”“不可谅解”;当他与高村霞的“肌肤之亲”不可逆转而且愈演愈烈、如火如荼的时候,他逐渐解除了心灵的枷锁,挣脱了世俗伦理的桎梏,高蹈于情欲铺张的舞台;最后,他将工作和迷恋女人当作人生不可或缺的事情,二者同等重要,都需要热情和“特殊的耐力”,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便是伊织的人生圭臬和情爱哲学。
“世事一场春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诗句),一年的光景,情欲之花悄然绽放,在其最璀璨的时刻,合乎逻辑地无声凋零了,留给这个情欲场中的男女空虚、寂寥、怅惘的情愫;一年的光景,何尝不是匆匆短促的人生的浓缩,尽管热烈地爱过,不知倦怠地享受过肉欲之欢、“人情”之乐,但这一切不过是生命过往中的雪泥鸿爪,如一年一度的樱花开落。相对于永恒的人生之痛,情欲之欢何其短暂。无论是伊织还是高村霞,在他们尽情享受爱欲盛宴的同时,负罪感、内疚感总是如影随形;尤其是这段情事结束之后,那种剪之不断、挥之不去的感伤酝酿成彼此心头的别样滋味。但终究也是短暂的,因为至少“伊织并不灰心。现在虽然遭受挫折,但将来恢复勇气之后,虽然明知是一片雪,也肯定会再去追求新的爱。”[16]
三、花与人、情同一:审美同情观照
《一片雪》中写了两类花,即随时令而变化的插花和自然开放的花。前者品类繁多,计有山茶、晚香玉、芍药、萍莲、睡莲、菖兰、紫菀、银莲花、蔷薇、霞草、六月菊、勿忘我等等;后者则为樱花。日本人从花开花落、草木荣枯、四季轮回中去感悟自然美和色彩美,因此,对“花”,如同“月”“雪”一样,有一种微妙而独特的情愫。日本人爱花、惜花,并玩出了最精致的插花。中国人也爱插花,其极致的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日本人却是“且雕且琢,复归于朴”。而在插花色系的选择上,中国人似乎较为随意,日本人则偏爱白、紫、青等色。在高村霞的插花中,白色和紫色是主色调。小说中的高村霞是渡边作为美的理想和美的典型来塑造的,插花一方面反映出她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追求,同时又是她自身美的多元属性的体现,以花喻人,花与人同一。如山茶,“这种山茶像茶花,但却不是茶花。它只开一朵白色的花,但却开不满,只是保持吊钟的形状”,因而别有一种“羞涩的风姿”[17];伊织“感到在暮色中插花的霞恰恰宛如一朵山茶”。[18]晚香玉的净白与幽香、芍药的妩媚与素雅、萍莲的娇柔与绰约、睡莲的清雅与脱俗、菖兰的袅娜与简淡,还有紫菀的风姿流韵、勿忘我的如梦如幻,等等,莫不是高村霞这一唯美典型与花的完美互渗和她性格特质的多层面折射。樱花之于日本,自不必说,其本国的作家,几乎没有不写樱花的,就连鲁迅先生在其回忆散文《藤野先生》中也写道:“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极简,极传神。《一片雪》中,樱花的出现在最后的回目“花冷”时,写的是雨中的樱花:
好容易才分开放的樱花还没来得及炫耀它的美丽,就冷落风雨,飘零而散,未免过于残忍。早知如此,莫如不开,但樱花却执着地盛开着,整棵树的花朵像着了魔似的争相绽开。
……
现在却冷雨浇花。温暖的春天里,樱花过于鲜艳,其它草木几乎无立足之地。造化之神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才令暴风骤雨摧残樱花。[19]
在盛产樱花的国度,樱花简直可以作为日本美的标识之一。但日本人欣赏樱花的美,不是花团锦簇、绚烂绽放时的美,而是风中曼舞、无声飘落时的美,甚至是“零落成泥碾作尘”时的美。是一种消逝着的美,一种虚幻的美。伊织怅望着雨中的樱花,自然想到霞,想到这一年来他们之间的爱欲缠绵,这曼妙的一页似乎刚刚掀开,却无可奈何地匆匆合上了。不消说,这雨中的樱花,不恰似伊织与高村霞这一年的情路历程的形象写照么?
在品式繁多的插花和雨中樱花的描述中,花与人、花与情契合无间,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日本美和带有东方色彩的“审美同情观”。东方民族继承和延续了原始思维的“万物有灵观”“互渗律”和“生命一体化”等观念,用“以己度物”的方式来认知世界,认知外界自然事物。东方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延续了原始时期的宗教信仰、社会结构、风俗习惯、伦理制度、政治体制、生产方式、生活模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等等,这样就使得东方艺术保持着与而原始艺术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正如邱紫华所言:“相对而言,亚洲、北非各民族由于在发展的历程中,原始时期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影响深重,生产生活方式和政体结构变化很少、很缓慢,在文化艺术方面继承就多于创新,各民族之间一致性的因素相对地就多于差异性的因素。这种一致性和传统性的文化特点,就在于它们继承和发展了原始审美思维和原始艺术表现的基本特点。可以说,原始审美思维和原始艺术表现的基本特点在东方各民族成熟的艺术和审美思维中较完整地继承下来了,并成为联系东方各个民族审美思维和艺术表现的共同性的纽带。”[20]在东方民族看来,人与自然原本一体,天然同一,没有主客观之分,更不存在隔阂与鸿沟。形成了“心物一元论”,“天人合一”,有限与无限同一的哲学思想。在古代印度中就有“你即他”“我即梵”“万物皆梵”“梵我一如”等命题;古埃及有“万物生命轮回”;佛教有“万物皆有佛性”;中国有“齐天地”“天人合一”“天人相类”“天人相通”“万物负阴而抱阳”诸说。表现在审美理念上,则形成了东方审美同情观。具体地说,就是“把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自然力加以拟人化或人格化,赋予它们以人的意志和生命,把它们看成同自己一样具有相同的生命和思想感情的对象。”[21]这种以自然万物与人同情同构、物我不分、物我同一为特点的审美理念与西方以“心物二元论”哲学为基础的“移情说”有了本质的区别,东方文学、艺术的诗性特征正是在这种文化空间中才得以呈现。《一片雪》中的插花和樱花正是典型的东方审美同情观的诗意呈现,即以花喻人,以花言情;花、人、情三者遂如水乳交融,不分彼此。
四、那一片雪:“美”与“物哀”双重隐喻
在《一片雪》中,写到雪的文字少之又少。小说的开头写道雪:“街道上蒙了一层白雪,就连跟前停的小汽车上也积了白雪。”“在朝霞的光亮中,有一片雪花正在飘落。不过,看样子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下。”[22]结尾处:“伸出手,那片雪竟然能够落在掌心,但在握住它的那一瞬间,它就完全消失。”[23]然而,小说偏偏以《一片雪》为题,实在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我们知道,对自然美的敏锐体悟形成了日本民族最初的审美意识,叶渭渠指出“这种自然观和美学思想,成为日本文学把握自然和创造艺术美的底流。一般来说,自然美包括山川草木、日月星辰、人的感情乃至人体的美,即宇宙万物。但日本文学尤以‘雪、月、花’作为其自然美乃至整个美意识的核心。日本文坛有一句名言,就是‘雪月花时最怀友’,对‘雪月花’的自然美倍感亲切,一般认为,‘雪月花’最能表达四季时令变化的美,这是有其传统的。日本文学描绘自然,以‘雪月花’为最多、最美、最热烈。‘雪月花’不仅是文学创作的主要素材,而且是美意识的传统。日本文学家以‘雪月花’同文学的抒情性融会贯通,展开日本文学具有独特魅力的美的世界。”[24]叶氏之论是符合日本文学事实的。“花”“月”姑且不论,单说“雪”,日本知名作家几乎没有不写“雪”的;雪景也不必说,即以“雪”为关键词和中心语来命名的,亦可信手拈来,如川端康成之《雪国》、崎润一郎之《细雪》和三岛由纪夫之《春雪》等。这三部小说有许多共性:其一,都是以爱情为题材;其二,无论是三岛由纪夫的古典式爱恋模式的呈现,还是崎润一郎的近代爱情歌咏,抑或川端康成的现代爱情唯美式表述,都带着感伤情怀和或浓或淡的哀思,在悲情氤氲的爱情故事中表现日本传统的“物哀”思想;其三,“雪”无论作为小说的关键词和中心语,还是作为景物的描写或氛围的营造,都涂抹着悲哀和苍凉的色调,弥漫着绵绵无尽的愁丝恨缕。而《一片雪》无论是题材、情感指向,还是其隐喻空间,都与《雪国》《春雪》和《细雪》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谓殊途同归。
《一片雪》中伊织的情感世界和情爱纠缠,注定是一种宿命式的悲剧结局。既然从家里搬了出来,就意味着打定主意终结与妻子的感情和婚姻关系,离婚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与笙子的四年之爱,似乎有“修成正果”的可能,但由于高村霞的介入,她的离去也是不可避免的;与有夫之妇高村霞的恋情从一开始就可以预见结果,当她的丈夫的女儿熏子将她与伊织的婚外恋情告知其父的时候,这段持续一年的爱欲纠缠,也顺理成章地依着其正常的轨道走向终点站。绚烂凋零,华美落幕,“树倒瑚狲散”,正应了《红楼梦》十二支曲最后一首《收尾·飞鸟各投林》中的句子:“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且,这不过是“一片雪”,一片春雪,无声飘落,悄然融化。伊织“回顾过去,自己和妻子的爱,和笙子的爱以及和霞的爱竟然没有实感,连着一片雪都不如。”[25]“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留给伊织的只有无边的空虚、寂寥、怅惘和自省——“觉得自己卑鄙狡猾,自私好色,是个集世界之恶于一身的家伙”。[26]如果说,渡边早期小说中所写的他的故乡北海道的雪弥天漫地,营造着一种迷惘、寥阔、朦胧的言情空间。那么,《一片雪》中所写的东京的雪则是些微的、零散的,稍纵即逝的,这就给整篇小说蒙上了一层虚幻、悲情的色彩;小说开头的雪,带有谶语式的暗示,而结尾处的雪则是男女主人公爱欲悲剧的宿命式的注脚,实与前文所述的雨中樱花具有互文性。
因此,“雪”作为文学意象和自然美范畴的核心之一,在《一片雪》中就具有了双重的隐喻。一方面,雪的晶莹、洁白与日本人对白色崇尚有关,白色象征着纯净、神圣、光辉、真、美等等。《一片雪》中的爱情,在道德伦理弱化甚至被忽略的日本,是与“雪”的象征内涵相一致的,在小说对于爱情的叙事中,没有物欲,只有人情,是“真”的,更是“美”的。而爱情终归寂灭,如同那一片雪的融化,及时行乐的短暂欢愉与接踵而来的空虚、惆怅以及失去后的无尽哀感、愁思如影随形,从而,这“一片雪”也就蒙上了悲情的色调,而进入日本传统“物哀”的审美空间。“物哀”是日本人在中国古代“物感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叶渭渠通过对《源氏物语》的整个题旨的分析指出了“物哀”思想的多层次结构:“第一个层次是对人的感动,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第二个层次是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对人情世态,包括‘天下大事’的咏叹上。第三个层次是对自然物的感动,尤其是季节带来的无常感,是对自然美的动心。”[27]很显然,《一片雪》中“雪”的审美指向主要在“第一个层次”,其中也有“第二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因为,小说除了爱情主线和主旋律之外,也有世相的呈现和四季的感怀。由此可以说,渡边淳一以“雪”为母题,与川端康成、崎润一郎之和三岛由纪夫之等文学大师联袂将日本平安时代的文脉延续至今。由此,我们看到,渡边这位坚守日本文学传统和传统日本审美文化的作家,以《一片雪》精心构筑了日本美的传统及其固定模式。
——本文刊于《华中学术》年第2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诗性之维:后现代艺术与东方艺术的‘家族相似’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日]渡边淳一:《一片雪》,高珊、郁贞、何英、秦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第41页。
[2][日]渡边淳一:《一片雪》,高珊、郁贞、何英、秦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第58页。
[3][日]渡边淳一:《一片雪》,高珊、郁贞、何英、秦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第页。
[4][日]渡边淳一:《一片雪》,高珊、郁贞、何英、秦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第页。
[5]祝大鸣:《双面日本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第页。
[6]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7]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8]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9]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10][美]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11][日]松尾芭蕉等:《日本古典俳句选》,林林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12]邱紫华:《东方美学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页。
[13][日]渡边淳一:《一片雪》,高珊、郁贞、何英、秦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第页。
[14][日]渡边淳一:《一片雪》,高珊、郁贞、何英、秦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第页。
[15][日]渡边淳一:《一片雪》,高珊、郁贞、何英、秦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第页。
[16][日]渡边淳一:《一片雪》,高珊、郁贞、何英、秦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第页。
[17][日]渡边淳一:《一片雪》,高珊、郁贞、何英、秦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第4页。
[18][日]渡边淳一:《一片雪》,高珊、郁贞、何英、秦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第5页。
[19][日]渡边淳一:《一片雪》,高珊、郁贞、何英、秦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第页。
[20]邱紫华:《东方美学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9页。
[21]邱紫华:《东方美学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46页。
[22][日]渡边淳一:《一片雪》,高珊、郁贞、何英、秦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第1~2页。
[23][日]渡边淳一:《一片雪》,高珊、郁贞、何英、秦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第页。
[24]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35页。
[25][日]渡边淳一:《一片雪》,高珊、郁贞、何英、秦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第页。
[26][日]渡边淳一:《一片雪》,高珊、郁贞、何英、秦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第页。
[27]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转载请注明:http://www.longhaishizx.com/lhszz/7224.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