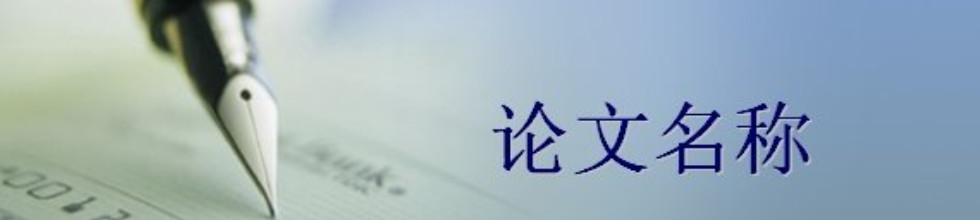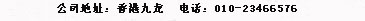厦门吃海记死了都要爱的海蜈蚣
沙蚕在闽南主要有三种,疣吻沙蚕Tylorrhynchusheterochaetus;全刺沙蚕Nectoneathesoxypoda;日本刺沙蚕Neanthesjaponica,皆属环节动物门多毛纲游走目沙蚕科,俗称还有海虫、海蛆、海蚂蝗、禾虫、水百脚、沙钻。
疣吻沙蚕(庄南燕绘)
它们举办失乐园式的极乐婚礼
海边囝没有不识海蜈蚣的,它是万能鱼饵。在潮间带沙泥交混的地方,很容易挖到它。尤其污秽恶臭的地方,例如海边污水口下,翻开石块,你就会看到它们成群盘踞交缠,长可数寸,狰狞而粗肥。
一
海蜈蚣正名叫沙蚕,实在有些溢美。用蚕比喻它的节状软体,略近形象。若论恶心感觉,还不如其他别名——海蛆、海蚂蝗,来得神肖。
它确实很像蜈蚣,形体怪异,呲牙咧嘴,须毛怒张,扭动起混杂惨绿猩红怪黄的酮体,一身密密环节泛发奇光异色,体侧的肉质毛刺如百足蠕蠕晃动,十分骇人。
早年钓鱼时,捏着黏腻腻的它,套入鱼钩,再用指甲掐断,是相当需要勇气的。我也曾内心惊栗而发抖,只是海脚孩子,在众人面前不能表现出怯懦。
三十多年前我到同安吕厝公干,农家好客留饭。主食炒米粉,炒米粉的佐料,在胡萝卜丝、高丽菜丝之外,有金针般焦黄的菜段,异常香鲜,咀嚼起来滋味越发深长。
问是何物,主人说沙蚕。
“海蜈蚣?!”
“对,海蜈蚣。晒干了,油炸。”
原来那狰狞恶心之虫,竟是可心美食!
禁不住再下箸,心里还是发毛。
当时不知道,闽南人其实从古早起,就有食用这丑恶美味的习俗。
地处淡海水交接的九龙江口一带,盛产沙蚕,名称涂虫。每年夏秋,渔民挑桶在石码沿街巷兜卖,涂虫们尚蠕蠕扭动,舞爪张牙,吞吐涎沫,发出细微嚣声,依桶壁攀行。
阿婆阿婶把它买回家,在盆钵里洗净滗干,加少许酱油搅动,涂虫肥满的腹部绽裂,白膏绿膏就流淌出来。煎熟后,锅底一摊黄白如煎蛋,虫皮俱包在里面。孩童放学回来,大人说是煎蛋,香喷喷食不绝口之后,方据实以告:此乃涂虫也。
老石码人说,生殖腺成熟的沙蚕,当地从来视为营养珍品,三四十年前,一斤也就几分钱。对吃不起鸡鸭的贫民们来说,实在是滋补美味。
民国《厦门市志》记载厦门人的食法,大同小异:“以杵臼舂去其腹中细肠,洗净爆干。食时以油炒之,酥而甘,亦佳馔妙品也。”晋代郭义恭在《广志》介绍的方法似乎最简单:沙蚕“得醋则白浆自出,以白米泔滤过,蒸为膏,甘美益人。”
平潭岛西沙滩,盛产大种沙蚕。当地人挖来后放到淡水里吐沙,以一根筷子从尾孔插入,翻出污物。晒干了,色金黄而透明,号曰“龙肠干”。用它炖汤,则色白如牛奶,味极鲜美,是当地高级宴席的珍贵名菜。龙肠干束捆,是走亲戚贵重的酬答礼品。
福州菜里原来也有“炒龙肠”一菜,颇为有名。后来大概是离海日远,沙蚕接续不上,就用鸭肠充数,味道相差甚远,慢慢就无人问津了。
二
査翻了一堆典籍,才知道长期食物不足的中国人,其实很早就食用这鬼物,唐代起间有记载。
明代《闽书?闽产》说,“泉人美谥曰龙肠”。也有地方称它凤肠。
清代施鸿保《闽杂记》里把它写做“雷蜞”,不知是否福州方言的记录。
龙海渔民的叫法最有意思,他们称之为“猫腱”,即猫的胗。猫的胗和青蛙的毛,都是子虚乌有之物,闽南人说虚幻之物,就以“猫胗水鸡毛”喻之。大概龙海渔民认为,这东西怪异得不可想象吧。
最详尽讲述这鬼物的,应该是清代赵学敏。他在《本草纲目拾遗?虫部》记录了它,称为禾虫。“禾虫,闽广浙海滨多有之,形如蚯蚓。闽人以蒸蛋食,或做膏食,飨客为馐,云,食之补脾健胃。粤录:禾虫状如蚕,长一二寸,无种类,夏秋间,早晚稻将熟,禾虫自稻根出。潮涨浸田,因乘潮入海,日浮夜沉,浮者水面皆紫。采者以巨口狭尾之网系于杙,逆流迎之,网尻有囊,重则倾泻于舟。”
赵学敏的描述,与我在石码的调查,完全相同。
禾虫所以水稻将熟时“自稻根出”,乃是彼时水稻必须干田控蘖、精饱稻粒。已经适应这种节侯规律的禾虫,那时也性成熟了,于是顺水入海繁殖。
石码老人说,尤其是农历九月半之后的天文大潮,海水漫入稻田,于是禾虫泛起,污泥浊水里到处浮游、蠕动着这鬼物。渔民在沟渠的涵口设网兜捕,多时一天能捕得百十斤。
沙蚕有十几类四百多种,皆喜栖息于有淡水流入的潮间带沙泥中,幼虫食浮游生物,成虫以腐植质为食。而能进入淡水稻田的仅有两种,即疣吻沙蚕和多齿围沙蚕。
临近生殖的沙蚕,躯体中部因有精子或卵,膨大为便于游泳的扁形,体色也变化了。雄虫背黄绿而腹乳白,雌虫背蓝绿而腹黄绿。雌雄皆通身斑斓鲜艳,犹如奢华婚服。它们等候着夜间上升到海面去,在那里行大婚仪式,交欢繁殖,排出性细胞,而后立马死去。
——也就是说,婚礼,同时也是葬仪。
惨绝寰世啊!
沙蚕当然不能放过这销魂时辰,它的婚舞极为动人心魄:
阴惨惨月光下,千千万万幽灵般的沙蚕,在海面浮游泛动。多条雄虫,围绕着一条雌虫欢蹈旋舞。一群群都为情欲与哀伤所激奋,倾尽全力疯狂扭动躯体,激起了一片片微小涟漪。那是海洋里的曼珠沙华,盛开于阴阳两界交接处的彼岸花。
它们在辽阔洋面上,一年年上演这炽烈的生死交代之舞!千年不变的海浪律动晃荡不息,潮声有似助歌,不知是赞颂,还是悲吟。
还有些种类,是在洞穴里交配的。雌体排卵后即死去,遗体则被雄体所食,而存活下来的雄虫,必须承担起孵卵义务——这是非常残忍、但是似乎合理的社会分工。
三
营生于稻田的沙蚕,在农药、化肥大量施用后就消失了。二十多年前,精明的福清人开始人工养殖沙蚕,出口日本韩国做鱼饵。这些年漳州也开始大规模养殖,用作养殖对虾亲虾及其幼虾的饵料——变换成另一种形态,绕一个圈子进入人类肠道。
我认为其实不必如此大费周章。沙蚕,不,龙肠呀凤肠,这诡异的美味,只消像吕厝农民那样稍事加工,就可以重回闽南人餐桌。
也可以更大胆一些,像老石码人那样直接食用。许多看起来很可怕的食品,例如蜂蛹、蛴螬,喜欢了那味道,就不害怕了。
在闽南语系人口为主的浙江苍南、玉环,青蒜炒海蜈蚣还是当地名菜。福建人现在公然把沙蚕端上餐桌的,大概只有莆田、福鼎等少数地方。莆田的一些地方端午节一定要吃炒面,而炒面里一定要有海蜈蚣。
沙蚕料理是福鼎点头镇的名菜,菜式多种多样:剖肚洗净的沙蚕,被用来凉拌、油炸、煮汤、干炒。经典做法是将海蜈蚣与酸菜一起烹饪,鲜酸可口,好吃得让你叫不要不要。那里的沙蚕干因此价格高企,一斤要五六百元。
《异鱼图赞补闰集》里说,沙蚕“首尾无别,穴地而处,发房饮露、未尝外见。取者惟认其穴,荷插捕之。鲜食味甘,脯而中俎。”莆田一带叉捕沙蚕,就用这种荷插之法。如今天然的已经很少了。不久前我去霞浦,县水产局介绍,有一户就养殖了三百亩沙蚕。
厦门文史界前辈龚洁,是有几十年钓龄的老海钓。有一天我们同席吃饭,说起海蜈蚣,他立时兴奋起来:
有一次他在小磴和角屿之间海面钓鱼,看到一条一尺来长的东西,俯仰泅游穿浪过来。网起一看,竟然是一条硕大无朋的海蜈蚣,大拇指一般粗肥。
本欲留作钓饵,渔民说不行——这种海蜈蚣太大了,肠液太多,鱼钩挂不住它。但是它是那么肥嫩啊,于是就在船上,以白水烧汤吃。
龚老说,那个鲜呀,你就打我三个巴掌,也不会吐出来!
他说的海蜈蚣,是另一种大型种,土名岩虫,《异鱼图赞补闰集》叫它“土穿”。红色的岩虫,叫红沙蚕;另一种遍体绿莹莹的,叫青沙蚕,则长在深厚的淤泥里。
沙蚕家族里的最大者,其长三尺。闽南之外地方,食用的沙虫,多是这类大型种。
文章引自即将出版的《厦门吃海记》
作者简介:朱家麟,日本立命馆大学社会学系(应用传播学专业)博士、博士后,原厦门晚报总编,厦门日报副总编。
LOOKERS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欢迎
转载请注明:http://www.longhaishizx.com/lhszz/66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