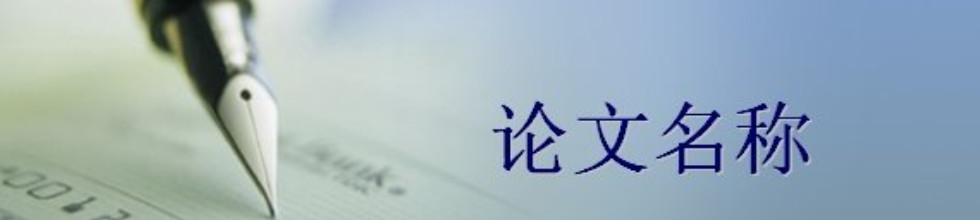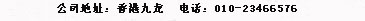一位91师老兵的龙海寻亲回忆
来源:龙海市 时间:2020-8-9
白殿风怎么治才能好呢 http://www.zgbdf.net/baidianfeng/zhenduanjianbie/22045.shtml
上一篇文章: 喜讯今年起,龙海提高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下一篇文章: 龙海最美村庄在哪里你最有发言权快来为
文
罗荣
我于年冬参军,在91师团(代号部队,后称部队)2营4连服役。年正月初三,连队开赴师部紫泥农场屯垦一年。七月份,我请假去角美镇照像,因天气炎热,途中饮用了不干净的水,归队后突发菌痢,上吐下泻,十分危重。农场军医急救后,决定送漳州医院。傍晚时分过农场与石美之间的海峡,从上岸并在等车过程中,当地渔民给我喂盐开水并宽慰我,此情此景让我终生难忘。如今重述我的军营生活和难忘历过并能在我离开龙海的45年后发表于我曾服役的地方知名公号上,如能找到当年帮我的乡亲们,也算还了我积在心中多年的心愿。感谢福建!感谢漳州!感谢紫泥!感谢石美!感谢《悦色书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中秋的午夜,到了我站岗的时间。背上枪和子弹带,我走上了紫泥驻地的海防哨位。月亮髙高地挂在中天,清辉从碧蓝的天宇倾泻而下,我们的营房,浸浴在溶溶月色里。我的心中涌动着无限的感动,为了陪伴一个在海陬站岗的战士,中秋之夜的月色,竟然如此澄澈,如此皎洁。天地间的一切,几乎纤毫毕现。我看见空中有一群鸟儿,静静地由北而来,悠悠地朝南而去。这些鸟从千里之外的飞到了东海之滨,在这泥土也是紫色的美丽半岛上落脚。在月光中我想起了正月初三那天,我们连队从驻地光明山出发,冒着残冬的余寒,走向几十公里的师部农场屯垦。上了紫泥岛,我们与即将来临的春天竞走,脱下棉衣,穿条短裤,跳进水齐腰深的内港去捞海泥。一俟春暖,那些摊铺在晒谷场上的肥泥就孕育出粗壮的稻秧来。到了谷雨边,我和战友们雁翅排开,把这些秧苗栽进大田。在熙熙暖风和灿烂阳光下,禾苗扎根,分蘖,拔节,扬花,结穗,直至勾下沉甸甸的头。当年在飘带似的港湾中,鱼儿在不停地跳出水面,两只系在岸边桉树上的小船,在粼粼波光中摇晃。倘若是白天,港湾里就会有鸭群觅食嬉戏。鸭是遐迩闻名的金定鸭,放鸭的是金定村的一位老人。老人很慈祥,脸上总是漾着笑意。我在放水灌田时与老人相遇,总爱用当地方言跟他打声招呼:“老人夹(吃)未?”闽南话有点难学,“老人”被我喊成了“老郎”。“老郎”拍拍我的肩头:“夹好啦,夹好啦。你夹未?”我说我“夹过了”。有的时候,我还和老人坐在田埂上抽烟聊天,虽然他的话我大部分听不懂,但我们却能聊得其乐融融。在一道土堤的那边,有座鸭棚,鸭棚里喂鸭子的,是放鸭老人的孙女,一个漂亮而乖巧的女孩,她呼唤鸭群进食的唿哨,银铃般清丽,非常动听。土堤是地方与部队农田的分界线。地方农田间,港汊交错,炎炎夏季,常有莳田的村姑在港汊里戏水,她们的笑声有点浪,能飘过高高的堤坝,传进部队的营房……当年的我们总在傍晚时分走在泥泞的土堤上,跋涉几里路去场部看电影。那部唱腔优美的京剧《龙江颂》,让人百看不厌。“你往前看,你再往前看,别让巴掌山挡住了你的眼睛!”电影中的女主角这么说。农场地处九龙江入海口,饮用的龙江水,灌溉的也是龙江水,战士喜爱龙江,喜爱《龙江颂》,喜爱龙江人和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龙江精神也就很自然。龙江水还带给我们另一个乐趣:夏秋天里,每当潮水上涨,岛上的龙江水闸关闭,营房旁边的水井干涸,炊事班总能从井中捞起大半铁桶胡子鱼来。紫泥有着一条绵延十几公里的石堤,在节假日,我喜欢到堤上去看海。那个地方,海鸟在空中盘旋翻飞,鱼儿亮着银白的身子,一群群越出海面,窜向远方。海堤下,长着盘根错节的红树林,林中栖息着无数的白鹭和灰鹭。若逢退潮,就有渔民去赶海,他们的鱼篓中,装着弹涂鱼、小鱿鱼,以及螃蟹和虾。对了,还有鲎,一种很古老的海洋节肢动物。我曾经和三位出公差的战友驶着一只满载着煤和黄土的木船,在风浪中飘摇起伏。出于对大海的无知,我们不顾渔民的劝阻,把船摇出了石美渔村避风的港汊。当船驶出到强风横吹浪涛汹涌的海面时,我们才明白我们的无知和冒失。那只装载过重的木船,此时想调头回港已无可能,只要船头稍偏,就有倾覆的危险。上千米宽的海峡,成为横亘于我们面前的生死线。有人提议卸载,因为海水几乎与船舷平行。有两条渔船飞快地摇到了我们的下风方向,船上的人高喊:“盲(莫)动!盲(莫)动!”此时卸载,是比贸然出港更愚蠢的举动。渔民们的及时赶到,让我们找到了主心骨,在渔民大声指导下,我们的船终于抗住了风浪,并赶在快飘出海口时靠了岸。当年的战友在紫泥的留影海堤往东,隔着海,远远的是厦门。只有我们班长在退伍前曾去过厦门,回来说,厦门是个美丽的城市,那里有陈嘉庚建造的集美大学,有鼓浪屿,有胡里山炮台。胡里山炮台对面,是金门岛。参军期间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厦门,只在暑季里去了趟角美,到镇上的照相馆照相。我在经过一年半的军营生活后,脸上的生涩已渐渐褪去,我得寄一张成熟的军人照回家。那天照完相,在回程途中,因天气炎热,我走得汗流浃背。一位赶牛车的农夫见我赶路辛苦,热情地邀我坐了一段路的车。到达农场对岸的石美村,我独自一人摇着小船渡过了宽阔的海峡。经过上一次的海上遇险,我已然学会摇桨驾船。我没想到,那天傍晚时分我竟然急病爆发,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头昏沉沉的。在农场军医紧急施救后,登陆艇把我送到了石美,医院派出的车来接我。上了岸,我听到身边有许多嘈杂的声音,那是去熟悉的闽南乡音。过了不久,有人喊我张嘴。我努力地睁开眼睛,看见身边围着圈衣衫有些褴褛的渔民,一个老大娘手上端着公鸡碗,慈和地对我说:“夹(吃)水,夹(吃)水。”我顺从地张开了嘴,我的口腔中缓缓流入的,是加了糖的咸盐水。老人喂完水,用手摸摸我的脑门,宽慰说,“莫代志的(没事的),莫代志的”。有人问我老家哪里,我说江西。那人叹口气,说,“这些北仔这么远来咱这当兵,确实不容易”(编者注:闽南人总把几乎所有外来的人都当北方来的,仿佛这里是中国的最南端)。我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那一刻,月光洒在他们黝黑的脸上,泛着古铜般的光泽……当年的我半个月后,我身体康复,重返连队。我特意经过石美村,我在当初被喂水的地方伫立了许久,我想向我帮助的乡亲说声谢谢。可那是个上工时段,渔民们都忙活去了,村庄显得一片静谧。咸湿的海风拂过我的脸颊,我的心中却浪潮澎湃。有流进口中的泪,如当时盐开水般咸湿……那年的中秋之夜,我没有按时交班,我只愿一个人守住这一轮让我思绪万千的明月。只是四十多年一晃间,自离开紫泥岛后,我再没踏上那座令我魂牵梦萦的海岛,再望一眼海边明月。但那碗盐开水,却一直滋润着我的心灵。推荐阅读:
龙海往事:“抖坛”与拖“厚壳仔”
那年,我在空八军看露天电影
三十五年前,学生时代的一次“公款”旅行
作者简介:罗荣,本名罗棣宁,江西宁都人。年参军,年退役。中国作协会员。年《解放军文艺》第4期发表小说《血证》、巜合坟》。悦色书声觉得不错就点个在看↘呗~
转载请注明:http://www.longhaishizx.com/lhsxw/5429.html
最新文章
今日推荐
- 没有推荐文章
热点关注
- 没有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