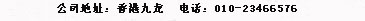小说丁龙海饕餮
年第6期(总第42期)
饕餮
文/丁龙海
作者简介
丁龙海,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石油作家协会会员,大庆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集一部、长篇小说一部。在《北方文学》《地火》《石油文学》《短篇小说》《章回小说》《延安文学》《青年文学家》《岁月》《娘子关》等四十多家报刊发表作品百余万字,被收入多种文集,小说、散文、纪录片等获省部级奖三十多项。中篇小说《又闻油香》获黑龙江省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一等奖。
这是哪里呢?他绞尽脑汁想,也寻不到印象。他放眼望去,空旷苍茫,望不到边际的草原……他颓废地坐着,天空灰蒙蒙的,没有风,空气阴冷,地面潮湿。
尖指碰到个小东西,他拿起来看,这是什么呢?外壳坚硬,椭圆光滑,纹理像蓖麻。他眼睛亮了,认出来了,几十年没见了……小小的杨拉罐,在炉盖上烤,几分钟后,用木棒轻轻一敲,就破碎了,一条金黄的肉虫,香气四溢,放在嘴里,甜甜软软的,那个香呀!什么时候吃的呢?是五岁?还是八岁?他想。杨拉罐长在榆树枝干上,不是哪棵树都有的,得走出村子很远,才能收集一小袋。铸铁圈套圈的炉盖,黑黑的油渍,是烤杨拉罐留下的。他敲开一个,弟弟的小手,就抓走一个,嘴角留着黄黄的汁液。姐姐不敢吃,远远地看着。他敲破一个,小心地拨去壳,一条金黄色的肥虫,在掌心蠕动。他托着让姐姐看,姐姐尖叫着,跑了。他笑得幸灾乐祸,把蠕动的肥虫,放在炉盖上,滋拉一声,金黄色的肥虫,化成了一股烟。弟弟吧嗒吧嗒嘴,瞅着他,眼泪要流出来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干打垒像散落的星群,散布在草地上。它们像是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冬暖夏凉。周末的晚上,虎逼高家门前,又支起了大灯泡,这个壮实的汉子,怎么叫这么个名呢?他们都背地里叫,面上得亲切地叫他高叔。夏日多蚊虫,天黑了,灯下飞来各种虫,高叔捉硬壳的黑老鳖。听大人们说,高叔特虎,在工地,青蛙、蚂蚱他经常捉来吃。一次,工地来了条狼,人们都躲起来了,只有他,拎了个镐头冲了出去……这是要出人命的,队长喊大家都冲出去了……狼跑了。高叔跺着脚骂,你们这帮蠢猪,狼给吓跑了吧!可惜了!可惜这狼肉了。
草原,曾经是狼的家园,而如今,它们变成了流浪者,危机无处不在,随时变成盘中餐、火炕上的狼皮褥子。
千禧年的时候,城里流行虫宴。油炸金边老鳖,让他想到了黑老鳖。虎逼高不是捉来喂鸡的,他肯定用来下酒的,他帮虎逼高捉了好多回,竟然被骗了。
鸟儿应该在天空,怎么都躺在地上。他神情慌乱,目光迷惘,怎么会这样呢?尸体、尸体,动物的尸体,分好类、排成行,像麦田似的……他仔细打量着,品种真多呀!黄嘴丫、红肚皮、红脑门、长嘴长腿的水鸡……最多的是老家贼。家贼四季都有,弟弟做泥球,晒干了,就是他的子弹。他打得准,弹弓有弹力,是医用的输液管。为了这条输液管,他在卫生所转悠了好多天,才偷出来。下雪了,他就从生产队拿个筐,木棍上绑条长绳,支起筐,下面放上谷穗。谷穗是秋天地里捡的,地是母亲和阿姨们种的,还种玉米、高粱、土豆,他喜欢种着黄瓜、西红柿的地,护地的阿姨,拿棍子赶都赶不走。
家贼家贼,就是个贼,不论它怎么贼,也是他嘴里的肉。
前排房的李四,在井队上班,每次休班,都拿把汽枪,满村子溜达找家贼。刚开始,小伙伴们新鲜,都跟在他屁股后。打下一只,一窝蜂地疯跑着去捡,谁抢到了,李四会让他摸摸枪,高兴了,还让放个空枪。他的汽枪,窝脖上弹,铅弹小,比黄豆粒大点儿。一次,李四打了三枪,没打着,房顶上家贼也没飞,煽动了几下翅膀,贼眉鼠眼耻笑着李四。李四急了,端枪的手有些抖了,瞄了半天也没扣扳机。他等得不耐烦了,抬手用弹弓,把家贼打得弹了起来,随后,就落在了瓦片上。李四端着枪,愣了半天,肯定在想,没开枪呢!家贼就吓死了!在他趾高气扬的时候,回过神的李四,转身就给了他一耳光,还抢了弹弓。他疯狂地扑了上去,李四一抬脚,他就飞了出去,如此反复,直到他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其实,李四对他挺好的,捉玉米杆里的小虫,在水边埋夹子,都是李四教的。李四有很多夹子,八号铁丝做的,还有大号的扣网夹子。李四淘汰的夹子,他去要,会给他几个。
春天来了,北方寒冷枯竭的土地醒了,鸟儿飞回来了。小学校在邻村,每天去上学,他都带上夹子,尽量设在离路边远的水泡边。夹子用木棍固定好,盖上浮土,玉米虫是诱饵,套在夹子头的卡扣上,鸟儿吃玉米虫,启动了机关,夹子就弹起,夹住鸟的脖子。他就曾没固定好,夹到大鸟的脚,夹子被带上天了。
家里有个铁丝网,支着四支脚,离炉盖一寸多高,是父亲做给姐姐烤土豆片的。后来,他用来烤鸟肉,连皮带毛扒出鸟肉,肉蛋蛋铺在铁丝网上,滋滋冒油,炉盖上滴满了油渍。为了争夺铁丝网,他和姐姐打架,衣服都让姐姐用炉勾子,划开过口子。
土鸡、野鸡、野鸭、野雁……怎么这么多,还有色彩斑斓的珍稀鸟类呢?他想,上中学的时候,他和伙伴们,半夜掏鸡窝,经常被人追着跑。后来,有了经验,先用棍子顶住门,就可放心大胆地偷了。土建队有几个南方知青,他们有煤油炉,很会做鸡。其实,就是鸡切块,白水煮,放点酱油、盐……怎么那么香呢?他叭达着嘴想。
参加工作了,他在井队打井,那是他人生最凄苦的日子。起早贪黑,板房冰冷,晚上打盆水,早上就冻成冰坨了。他很幸运,只干了一年,腿被砸折了,康复后被分到管修厂,当车工。师傅大他二十来岁,西北人,脾气暴躁,总说他死迷粗眼、不起烂山。过年的时候,母亲准备了酒和罐头,让他去串门。师傅留吃饭,酒喝开了,就说他不赖、精干。他有个师兄,老爹是保卫处长。师兄第一次带他去打猎,坐一辆吉普车,保卫处的干事开车,带了把半自动步枪和一把五四手枪。夏天,七月流火,天空的云朵,都晒化了。离开矿区,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师兄说,他经常去湿地打野鸭子,如果运气好,还能打到大雁。师兄膀大腰圆,给人孔武有力的外表,其实,他是虚壮,没多大力气。师傅和他说话,都用商量的口气,背地里,师傅说师兄,可油了、死迷粗眼的。师兄有个性,隔三差五来上班,也不换工服,像是来视察工作。师兄的枪法很好,锁定目标,叭的一枪,野鸭子坠落下来,他得屁颠屁颠地去捡。那时候,野鸭子真多,他试了两枪,还真打到了一只。三点一线,和弹弓有区别。两只白色的大鸟,在天上盘旋。干事端起枪,没见他怎么瞄,叭的就响了,一只大白鸟,翻转着落了下来。
他喜欢肉食,无肉不欢。食堂清汤寡水,只有年节,才有肉吃。师兄有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他都能吃到嘴里。冬天,师兄还去大兴安岭,打过狍子、鹿、野猪什么的。
师博说他不赖、精干。他也争气,学了两年,就独当一面,成了生产骨干。他发愤图强,考上了夜大。父母说他晚熟,怎么一下子,就长大了呢!其实,在井队时,他就给自己目标,要出人头地。什么是出人头地呢?就是有肉吃。
怎么这么快呢!三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从基层到县团级、一把手,他感念父母,可两位老人没福气,退休没几年,都相继离世了。姐姐在科级岗位上退的二线。弟弟早就下海了,做物资劳保。他懒得过问,弟弟磨他,他还得往关系单位打电话。弟弟给他送钱,他从没收过,媳妇收没收,他也懒得问。弟弟知道他喜食肉,就给他送肉,他很受用。弟弟有个私家会所,很会烹饪珍馐美馔,在那里,熊掌都不稀奇。对野生动物保护了,每道肉食上来,他只吃,没谁报菜名。来聚餐的朋友,都是有关部门有头有脸的,大家心照不宣、吃得心安理得。身体胖了,三高找上来了,心脏也快支架了,医生说少吃肉,海鲜还是可以的。于是,他的胃,成了海鲜的墓地。当然,有了好肉,他也会吃,什么是好肉呢?只有圈里的几个人知道。
他心里有个秘密,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觉得自己变态,不可救药了。那些日子,他特别苦恼,食之无味儿。一天,弟弟来看他,他说胃难受,没食欲。他问弟弟,知道寒食节吗?弟弟摇头,一脸迷茫。他说,晋文公归国,分封群臣,介子推不愿夸功,携老母隐居于绵山。后来,晋文公到绵山请介子推,介子推不愿为官,躲避山里。晋文公手下放火焚山,想逼介子推出来。结果,介子推抱着母亲,烧死在一棵大柳树下。为了纪念这位忠臣义士,晋文公下令,介子推死难之日,不生火做饭,要吃冷食,称为寒食节。他瞅着弟弟,接着说道,你知道介子推立的什么功劳吗?弟弟接着摇头,仍然迷惑地看着他。他说,晋文公落难的时候,几日无食,介子推把腿上的肉割了一块,同野菜煮成汤给晋文公喝,这可是救命之恩呀!他没有讲,齐桓公和易牙的故事,他觉得太惨绝人寰了,齐桓公该报应,让易牙给活活饿死。
几天后,弟弟打电话,说找到了治胃病的妙方,请他来会馆品尝。他去了,也吃了,不就是瓦罐闷的肉吗?弟弟不是介子推,他也不是晋文公。弟弟鬼祟地说,我咨询了老中医,要想治好哥的胃,胎盘最有疗效了。他的胃缩了几下,很快又复合了。品尝妙方后,他时常会梦到一头怪兽,形状如牛身人面,眼在腋下,虎齿人手,大头大嘴。这是什么怪物呢?他想,开始莫名其妙的,感叹命运了……人这辈子呀,说快也快,前些日子,他刚提拔个科长,多好的小伙子呀!名牌大学毕业,为了庆祝升迁,和同学们聚会,四十来岁,就心梗死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就不喝白酒了,都说红酒好,他喝着喝着,就习惯了。有个小品,演得特别好,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这些年,管得严了,他也觉得,自己的胃累了。
姑父去世那天,他梦到了一匹白色的马,撒着欢儿,在草原上跑。姑夫在马车队上班,不知道怎么,和姑处了对象。姑从老家来,是照顾他和弟弟的。姑夫第一次来家,他就缠着姑夫要吃肉,姑夫很为难。姑沉下脸,不开心了,杏目圆睁,两条粗黑的辫子一甩,说,我亲侄子,就想吃口肉,有这么难吗?姑夫国字脸,络腮胡,虽然刮过,下巴泛着青,像片胎记。姑夫讨好地嘿嘿笑,眼睛贪婪地盯着姑说,你说了,吃我肉,都行。一天夜里,他被乱糟糟的声音吵醒了,他光着脚下地,看到姑正开心地笑,地上特大的洗衣盆,装着满满的肉。多年以后,和姑夫喝酒,才告知他,马肉的来龙去脉。从那以后,他更敬重姑夫了,侄子想吃肉,姑夫就伙同几个人,谋害了一匹马。报到上面说,是病死的,埋在一个土沟里。晚上,他们就带着刀具,把马肉分割了。
前几天,多年不联系的师兄,约他去看师傅,说是弄了只大白鸟,到师傅家吃。师兄早就退休了,退休前,是一个科级厂的厂长。师兄喜欢电脑游戏,合伙搞了个网游公司,专门设计枪战。师兄带着厨子来的,专为大白鸟请的。师傅牙口不好,一口也没吃。师傅说,都怪师兄,野味吃伤着了。师兄打趣说,看我师弟,怎么吃都伤不到,这是口福,积来的福份。他喜欢吃这种紧实的肉,尤其那个肝,做得滑润可口,香味十足。他很开心,放下红酒,让师弟倒白酒,十年的茅台,难得喝到了。
他站起身,望着眼前的动物尸体,每一种,他都能叫出名来。他不敢说,也不能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么多一类、二类保护动物,说出去,后果是可怕的。他想到了触目惊心。
一只巨头怪兽,从天空飘落,它牛身人面,腋下的眼睛如血红灯笼。它环顾目周,突然,挥动双臂,腑部张开了,形成巨大的嘴,露出阴森虎齿……一股强劲吸力,在怪兽口腔发出,一瞬间,地面上的尸体,涌入怪兽口中。他的面前,连根稻草都没有,他拼命挣扎着。一粒杨拉罐,冲进了他的鼻孔里,令他窒息,他急忙往外挖……他的手被按住了,他听到一个激动的声音,快!快!给妈打电话,爸醒了,快!叫大夫。
他的手,抓着插在鼻孔里的氧气管。儿子的手,紧紧握着他的手。他用力睁开眼睛,疲惫的目光,对上了儿子激动的眼神。
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他拒绝任何来探望的领导、下属、亲戚。媳妇说,你这是何苦的呢?你又不知道是天鹅,师兄在公安局交代了,天鹅是他朋友送的,谁知道是毒死的呢!你算是捡了条命。媳妇从保温煲里,倒出了一碗汤,她用白钢小勺尝了尝,喂他喝。小勺离嘴近了,他闻到一种气味儿,涌进了胃里,什么味道呢?他感到恶心,胃里翻江倒海,要吐出来。他挥手,打飞了嘴边的钢勺……媳妇惊恐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这是怎么了,给你补身子,特意熬了一上午,你喜欢喝的飞龙人参汤。
他不敢闭眼,只要合上眼睛,就看到一头怪物,贪婪地吞噬着自己……他想起很多年前,在南方一座庙里,遇到一个老和尚。和尚慈眉善目地说,人呀,做什么,都是有定数的,身体如此!事业如此!钱财如此!吃喝也是如此!他相信人定胜天,觉得和尚可笑,就问,如果超过了定数,会怎么样呢?和尚笑了笑,请他进了一个房间,让他看一个青铜瓶……瓶体椭圆,有扁平浮雕,向上收口,铸造精密,两侧对称设耳,盖是个怪兽塑像。
他瞅了许久,不知所云,问和尚,盖上怪兽是什么?
和尚说,饕餮。
大庆市网络文学协会本期责任编辑 陈意超
转载请注明:http://www.longhaishizx.com/lhsrk/6269.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